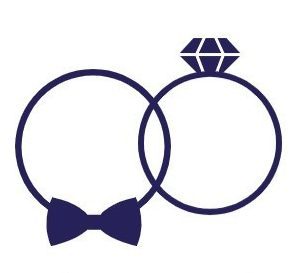我现在要说,正是在这样的世界中,最可贵的,是书呆子。
当代世界的基本原则是实利主义。一个人在这样的时代里生存,他的人生成就用什么来衡量?用资本或他的生涯与资本之间的联系来计算。我们在这个时代必须很聪明,而书呆子是聪明的反面。书呆子为什么不聪明?我这里指的主要是人文学科的书呆子。假如你捧着一本计算机教材在那里读得很努力,就绝不是书呆子,因为将来是可以用命令行来换钱的。假如你捧着一本叔本华的《世界之为我的意志和表象》,就绝对是一个书呆子。世界不是你的意志和表象!世界是要用计算机语言来构造的。
所以,我给书呆子下一个定义:
他们是一些生活、活动并且栖身于人文典籍的世界中的人。他们与现实保持着足够的距离。
这样的人,可笑不可笑?可怜不可怜?可悲不可悲?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讨论的主题。
你到底有什么理由栖身于那个人文典籍的世界中?回答就是:这是一个这样的世界,在其中收藏了一个民族在其历史进程中所拥有的种种思想、种种行动、种种信念、种种遭遇、种种奋斗。凡是能够被列为人文典籍的作品,的确记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命运,以及这个民族的思想、信念、行动、遭遇、奋斗、苦难。这种记载,意味着精神上的体验,文科的书呆子们就沉湎于其中。我们试问:如果你喜欢这种精神体验,并且能够理解这些典籍,难道可以把你判定为“不懂得人生”吗?
假如说,懂得人生只是意味着我们对现实社会中的利害关系、因果关系有一种清晰的了解,那么,这就是关于“懂得人生”的一种降格的说法。对于本民族的历史进程有深入的体验,并且能够理解它的人,难道不是在一种更加深刻的意义上懂得人生吗?这是全部问题的关键所在。
当然,体验只是体验,并不给出指导我们生活的金科玉律。倘若你拿一本人文典籍说“这就是我人生的指南”,你拿一本叔本华的《世界之为我的意志和表象》说“这就是我的人生指南”,肯定不能这样理解。叔本华的这本著作,代表了他对欧洲民族的苦难,对它的民族家园的重建的理解。这对我来说代表了一种重要的精神的体验,即对西方历史生活及其演变的精神体验,这种体验意味着一个民族探究真理的道路。你难道不愿意从这种探究中获得最大的教益吗?
人文文献是什么?一部人类精神史。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一个民族的历程,就是一部巨大的学术著作。这部著作是由它的宗教、艺术、哲学等方面的相互关联所构成的。所以,人文研究就是解读人类精神史。这种解读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这个时代让我们感觉到这种解读是无足轻重的空谈,是一种与现实生活无关痛痒的活动。
对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学者或书呆子来说,对民族历程这部巨著的研究,绝不是用来敲开利禄大门的敲门砖,而是一条理解、解释和批判生活的途径。
我们为什么需要理解、解释和批判生活?因为人的生存在根本上是有限的。不过,倘若我们仅仅是有限的,其他的也就不用多说了。问题是,人同时又渴望无限。这一点哪怕是对于“庸夫愚妇”也是一样的。芸芸众生中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渴望无限。要理解这一点,可以从爱情这件事情上说起。
假如你恋爱了,真正地恋爱了,你最真诚的愿望是什么?你一定希望这一份让你心驰神往的爱不会像朝露一般轻易地蒸发掉。你感受到爱是一种伟大的东西。凡伟大的东西,应该不朽。在此,我不是硬要把哲学的词藻用到男女之间的爱情上去。爱情的真相本来如此。你们两人爱得如此深切,而假定客观环境又压制着你们,阻止你们的爱结出现实的果实,你们能爱,但不能结合。这时候,在你心头涌起的最深切的愿望是什么?你会想:我们的相爱是一种奇迹,是千年注定的缘分,今生今世不能结合,还有来世的希望。让我们今生有约,来世牵手。来世是什么?是超现实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你自然而然地就超越了实际体验到的世界,自然而然地相信一种真正属于人生幸福的东西是超越当下有限的经验的。你此时不再愿意相信科学家对你说的那种万物皆变的自然规律。你不愿意相信爱情和一个苹果是一样的东西,它慢慢地成熟、丰满,而后又慢慢地腐烂,直到最后消失。你说:“不,我此刻不是一个科学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任何人逼迫你放弃对科学的信仰,而是因为你自己fall in love(坠入爱河)了,于是,你自然地成了一个人文主义者。你知道了爱情是什么,它既是俗世的、经验中的存在,又具有超越性。它是不朽的,但我们又希望这不朽的东西同时是经验地实现了的——正是在这种要求把超越与经验两个方面统一起来的愿望中,包含了爱情所固有的全部激情、向往和痛苦。
当代有思想家认为,在今天已没有真正的爱情。我以为,这样说恐怕太悲观了一点。据说当代人类的生存状况已把一切超越性存在都清洗掉了,于是,爱情的痛苦仅仅成了俗世中的烦恼。在爱情中的人不再有大悲大喜,真正的爱情悲剧也已消失。我不相信这一点,因为凡是有少男少女的地方,必定会有真正的爱情。爱情不会因为一个时代的特殊性质而被消灭掉。如果说在今天,传统的宗教信仰的超越性已在根基上衰落了,艺术的崇高性质已经丧失了其精神的源泉,而哲学在今天也已处于失语状态,那么还剩下什么呢?还剩下love!正是爱情,还继续把超越性存在提示给我们。
从love来看人生,就可以知道,凡人生的价值中必包含超越性。不仅是爱情,只要是属人的东西都包含超越性。我们怎样赢得对当下实际情景和当下实际利害关系的超越?通过一个领域中的活动,这个领域就是人文精神的领域。我们读一部小说,读一部史学著作,读一部哲学作品,我们获得了什么?获得了对超越性存在的感受和领悟。
阅读人文典籍,意味着激活我们心灵中的性灵部分。我们灵魂中最高的部分是性灵。假如你是一位人文学者,你进入历史,你读到的不仅是史实。你一开始可能采取科学的方式去读历史,总结某段历史时期大约有几个部分,梳理史实之间的因果联系。但这样读,还未进入思想,也未发挥你的性灵的力量。如果你不仅读到史实,而且读到一个民族在其历史上的悲喜交集的命运,你就可以明白,司马迁为什么这样表达历史研究的目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一个民族的悲喜交集的命运就写在它的史学著作中,它的哲学著作中和它的文学作品里,这是一个确凿无疑的基本事实。你从史学著作中读到了大悲大喜,时而哭泣,时而欢笑,外人一看:书呆子,这个人居然用书本的世界代替了现实的世界!
我们从史实中读到了悲喜,这种悲喜就意味着在事实之外的一份感悟。假如你对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感到悲哀,你一定感悟了什么。本来你与维新变法的年代相距很远,何须悲喜?但你确实有了悲喜,这就证明你对某种超越性存在产生了感悟,你感悟到了我们民族的近代命运。
我们读历史,读出了悲喜,就是有了感悟,就超出了事实的限制,进入了对超越性存在的领会。接下去你想做的事情,就是设法理解自己的悲喜的性质与意义。这就是说,你要把这些感悟上升为思想了。这种理解不是自然科学上的理解,而是进入了哲学。所以,史学研究与哲学相通。
我们不可能把我们今天中国人的生存状况看成是由天上掉下来的一整套规则所造成,我们知道,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我们还知道,这套规则在中国的展开方式与西方大不相同。这就构成一对矛盾:一方面,我们不是西方人;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用西方规则。我们在这种矛盾中感到痛苦,才想到要追寻痛苦的来历。这样,我们就进入了思想。
但是我们又发现,今天的许多人文知识分子正逐渐把学术研究变成一种纯粹知识的探究,成为一种很专门的职业,这是很让人感到悲哀的。在这种状况中,我们所能成就的至多是专业的知识,而不是对真理的探寻。